曾捐献全身4倍血量,新冠刚康复又6献血浆
2020年春天结束以后,蔡桃英和黄卫兵都不再是从前的自己。这对大半生都安于平淡的武汉夫妻陡然拥有了三重身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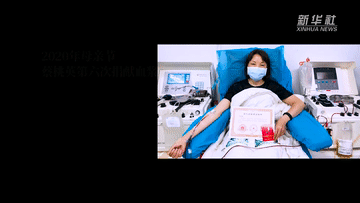
5月10日,母亲节这一天,蔡桃英走进武汉血液中心,第6次作为新冠肺炎康复者捐献血浆编辑本段
。编辑本段
与之前不同,这一次,她的血浆将被用于黑龙江抗疫一线。编辑本段
编辑本段
她和丈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第一批救助患者的一线医护人员,也是第一批因工作暴露感染新冠肺炎的患者。
微妙的身份转换,背后是对生命中至暗时刻的黯然穿越。
其中的安危,暗含着武汉整座城市在这个春天不应被历史遗忘的,悲欣苦乐。编辑本段
编辑本段
清明节清晨的这场攀登,50岁的黄卫兵用了往年两倍的时间。
武汉市新洲区三店镇的这座小山坡上,埋葬着他的奶奶、姥姥、爸爸和妈妈。每年清明节,他都会准时爬上山坡,健步如飞的样子,一如还是至亲们记忆中那个矫捷的少年。
这是他从汉口医院新冠肺炎病区出院的第44天。尽管十几天前,他已经回到汉口医院放射科工作,但爬上山坡,或任何需要体力的活动,都会让他气喘连连。

“我这只是肺的问题,我夫人的心脏还更严重些。”作为医生,黄卫兵这样评估。此时,他的夫人、同为新冠肺炎康复者的蔡桃英正陪伴在他身边。
蔡桃英是汉口医院内分泌科的护士,比黄卫兵早9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。蔡桃英因为多次捐献康复者血浆而被媒体广泛报道,人们惊讶于她高抗体的血浆“一次能救4个人”,
但几乎没有人知道,看似健康的蔡桃英,每天夜里都要忍受心悸心慌的无穷折磨。编辑本段
但没什么。
重要的是,此时此刻,还能与爱人一同站立在这草长莺飞的人间四月。
彼此逆光的身影里,惊心又庆幸,已然各自穿越过人生中至暗的时刻。

巨浪来袭 别无选择编辑本段
“1月20日前后的汉口医院,很恐怖。”黄卫兵这样说,“到处都是患者,门诊、急诊、候诊大厅、检验科、病房……到处都是患者!没有床位、没有座位,很多患者就一直躺在担架上……而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患者涌进来,潮水一样……”
“看不到尽头。”这是黄卫兵从医的第30年,他第一次在工作中“发怵”。
“不是怕自己被感染,而是那种无力感。”即便每天要看1000多份CT片子,患者还是“怎么看都看不完”。
“就如同面对山一样高的巨浪。”明知一己之力绝无扭转局面的可能,“但还是要做,只能一直做下去”。
此时的蔡桃英正忙于护理突然增加的、因各种原因住院的患者。当1月21日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,蔡桃英仔细回想,自己被传染甚至可以追溯到1月3日——从那天开始,她接手的多位病人被先后确诊。
“是那个糖尿病入院的年轻人。”蔡桃英猜测,“或者是之后70多岁那位病重的老奶奶,要不就是……”
“反正不重要了……”
其实,根本不存在那个致使她感染、改变她生命轨迹的“具体的”病人,因为“太多了”编辑本段
同一时期,汉口医院有50多名医护人员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。
“最多的时候,每天有1500多名病人,其中百分之70到80,都是这个病。”黄卫兵被感染前,核酸检测还没有普及,CT是确诊的主要依据,于是,为病人看CT片子、判定病情的他,成了巨浪来袭时,最先直面灾难的人。
1月30日,本来计划迎接夫人康复出院,但这一天,已出现发热症状的黄卫兵,被最终确诊。
心心念念的重聚,却成再别。编辑本段
十几年间义务献血数十次、认为自己“没问题”的黄卫兵,在巨浪面前,未能幸免。
意料之外,却是情理之中。
“那时别无选择。”黄卫兵说起明知存在巨大感染风险,还每天“疯狂”接诊病人,“别无选择,不是不能做其它选择,而是想都没想还存在其它选择。”
至暗时刻 独自穿越编辑本段
持续高烧一周后,黄卫兵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真正可怕的不是高烧本身,而是病情转重与死亡的关联不言而喻。编辑本段
“看不到尽头,也不知道结果。”入院后的黄卫兵,每天经历几乎同样的“折磨”。
一天的痛苦,开始于中午过后的高烧,38度、39度、40度……一直烧到夜里,随之而来的是呼吸困难。等退烧药起效,黄卫兵一身大汗,之后,筋疲力尽地睡去。清晨,精神稍微好一些,总算能喘口气。但高烧的午后,总不厌其烦地早早来临。
与之相伴的,是清晨的希望满满和深夜的几近绝望。编辑本段
“人在这种希望、绝望的轮回中,心力交瘁。”黄卫兵在每天清晨理智地分析病情、享受亲友的关爱,在心中注满希望……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深夜来临混乱迷离的高烧中,认定黑暗无有尽头,质疑哪怕微光的存在。
周而复始。
黄卫兵以为蔡桃英对这一切,并不知情。他在与妻子的通话中,几乎什么都不提,
只一条心打定主意“自己扛”,直到最后。编辑本段
几乎就在同时,妻子蔡桃英也打定了同样的主意,同样也是只字未提。
自己患病期间看书、聊天、安慰病友的蔡桃英,在丈夫的持续高烧中迎来了人生的至暗时刻。
一直信奉“面对灾难,苦恼无济于事,不如泰然处之”的她,在丈夫确诊的那一天,问自己,“为什么所有的坏事都一起来了?”
当黄卫兵一夜一夜在高烧中屡屡绝望的时候,守在家中的蔡桃英,
就一夜一夜,隔着整座鲜少有人活动的城市,陪他流泪到天明。编辑本段
你无从知晓,同样的夜里,武汉有多少对爱人,如此消磨。编辑本段
至暗时刻的骇人之处,不在于它的突然降临,不在于它的不容商量,甚至不在于黑暗吞没你所拥有的一切,而在于,对残存希望的否定,清坚决绝。
当一个人长久置身于彻底的黑暗,不再拥有对任何事情的选择权,浮现在他心头、真正构成意义的,无非过往——做过的不多的几件事,爱过、陪伴过不多的几个人。
50岁的黄卫兵,最后,对自己的这一程,还算满意。
“一直做的就是救死扶伤,不论是不是疫情,该做的都做了,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,这辈子,值了。”
就这样,又过了几天。
高烧终于不再来临的那个午后,黄卫兵内心激动得像个孩子。
打通蔡桃英的电话,他却只说,“不烧了”——好像从来没有担忧过死亡,和只身陷入无止境的绝望。
蔡桃英说,
“太好了”——好像从来没有整夜流泪,和茫然于此后的人生何去何从。编辑本段
托以死生 无有恐惧编辑本段
黄卫兵治愈回家的那一天,蔡桃英仍在居家隔离。不能出门,她便倚门“等待他的脚步声”,“竖起耳朵听”。
这是他们相识的第27个年头。
毕业于同一所学校,工作于同一家医院。在工作中相识、相爱,决定共度此生。
从来平淡如水。
只在这个春天,顿起波澜。
穿越过人生的至暗时刻,再相互搀扶爬上埋葬故人的小山坡,心中别是一番滋味。
“怎么春天这么美?!”编辑本段
好像一切都是“偷”来的幸福。编辑本段
清明节上午10点钟,小山坡上的黄卫兵和蔡桃英被全城的鸣笛声深深淹没。
此时此刻,这个声音正响彻整个中国。
“死里逃生”,经历过至暗的时刻,黄卫兵说,“生活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。只是现在,更清楚生命的价值,更确定自己做的事情,值得用生命去托付。”
其实,我们,我们和同事,我们和这座城一直同在。
而且,“心中再没有恐惧。”
清明祭奠结束,蔡桃英扶着黄卫兵,慢步走下小山坡。黄卫兵微微的喘息中,武汉恢复了日常的宁静。
经历了这一场,这座城市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不同。
